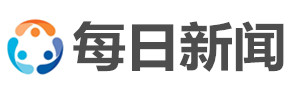本篇文章1214字,读完约3分钟
很难判定艾未未的身份。 可以说他是名人之后——诗人父亲的蓝头光环不一定受到缪斯女神的喜爱,至少是时代的产物。 他也可以说是建筑设计师。 他是成为国家体育馆鸟巢的中国顾问,“艾未未”一夜之间被普通中国人所熟知,在这个光环闪耀的期间,他在卡塞尔文献展的大草坪上竖立的巨大的门状装置没有被微风吹倒。 可以说他是艺术家。 ——1979年,他的作品参加了第一届“星美展”。 2007年,他带着1001名来自各地的中国人来到德国的一个小镇生活了两周。 令人惊讶的是,用没有技术的人的海洋战略完成了其作品“童话”。 让德国人也用不标准的普通话认识了“艾未未未”这三个字。 顺便说一下,我让他认识了那部作品的作品。

现在他的身份鉴定越来越混乱——刚刚落下帷幕的崇尚学术著的“沙飞摄影奖”将“摄影创作奖”颁发给了艾未未。 那是否意味着从此,艾未未在其他行业难以确立的学术地位终于在摄影界得到了意想不到的认同? 复旦大学的顾铠教授这样解释道。 “1983年至1993年艾未未未及的个人影像记录,承载着当天中国人特有的真正“离散”感,个人被投入到了另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 他以个人史的视野切入异国文化的纽约,是个人与时代发生的对话与共振。”

“采用摄影手段持续关注社会和人类自身的命运,以及在推进摄影和影像采用方面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奖励取得优异成果的个体”,这是“沙飞摄影奖”的指导方针补充。 艾未未的摄影作品完全使用逆向摄影的语言,冷漠的构图,甚至完全无视构图,镜头直接对准生存环境中出现的一切,照片就像艾未纽约自然生活的排泄物。 就像达达艺术品想要给人带来某种“侵犯”一样,连美学都无视了。

持续引起争论也是反艺术的一种,达达主义的行为规范就是破坏一切。 艾未未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标准,据说他现在每天至少接受两次采访,接受采访也成了他“艺术”的一部分,但他的媒体经历从一开始就不是这样。 其中有一个从认知到重新认识的曲折过程。 最初阶段,对媒体他不拒绝,无论省报、县报、专业报,都热情应对。 进入第二阶段,他不接受采访,或者开始有选择地和媒体交往。 从而引起一定范围内的关注度、神秘感,给被拒绝的媒体带来秘密虐待的快感,而没有成为媒体间争论的人物。 第三阶段,也就是现在,面对媒体的策略再次上一层楼,用极具杀伤力的语言选择文芳阁的兴奋神经,以不在意麻烦细节为坦率招牌。 除了媒体采访外,他的业余时间是聊天、打瞌睡。

艾未未说:“艺术没有权力,只有希望赢得权力。” 现在,他凭借从自己的达达主义中学到的皮皮智慧赢得了中青媒体的话语权。
“有坏想法,也有看不惯的,也有恶毒的语言”艾未没有这样评价自己,他对外界、恶毒的语言和赞扬的语言也不关心。 恐怕这些都是用毒药攻击毒药或通篇称赞的。 因为相互矛盾的语言在彼此的潮流中形成的民众瞩目的漩涡,抬起了这个身材高大、留着胡子的北方莽汉,许多、虚实的头衔贴上了他身上奇怪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皇帝的新衣服。
标题:“东方早报:艾未未他究竟是谁?”
地址:http://www.t46t.com/mrxwyl/22826.html